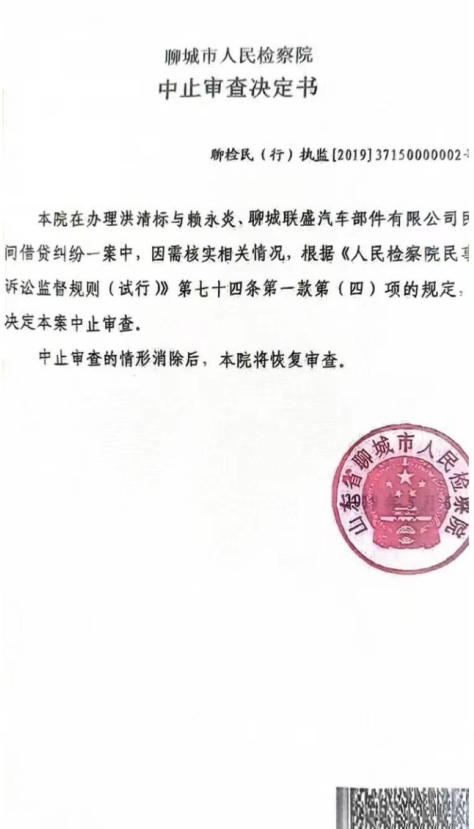深情的对抗者
看中华 最新资讯 2015-12-20 08:08:30
“每户人家都有新娘。多么久的等候。
我停止走路,远远地绕着圈子。
老马早已预知雷声
无力的闪电姗姗落地。
啊,这世界多么古老。”
在深夜读这些诗,眼圈发热,令人鼻子酸楚。像阳光一样,精神的慰藉既远又近,既温暖又悲凉。而它存在,并向你低语——“我在。我一直都在。”
他的爱饱含着悲伤
初中辍学,少年出家,数次自杀,几度入狱;出版诗集百多部,确立了他在当代韩国诗坛的地位。抑或说,他也在影响着世界诗歌的某种方向——他就是韩国诗人高银。
高银这样的诗人永远不会是过去时,尽管就在几天前,我曾问一位韩国诗人对高银如何评价,他的回答是:“高银算是传统的诗人,现在很多年轻诗人已经不再用他那种手法写诗了。”这样的回答无法改变我对高银的看法,他依然是那种人类的心灵永远需要的诗人,尤其当冷漠麻木的毒素遍布人群的时候,尤其当杀戮染红宁静大地的时候,尤其当大自然在城市蛮横的步履前沉默后退的时候,尤其当一个人感到绝望、感到一切皆为虚无的时候。他以柔情对抗冷酷,以人的尊严对抗暴政,以细腻到令人惊悚的感觉对抗陈词滥调的表达。他是一个对抗者,在荒诞不经的生活中,他是人类的一根纤细的神经,传递着人性中微弱又不息的希望。
《唯有悲伤不撒谎》是高银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诗集,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到十年佛门生活对他的影响,但影响更多来自他身处的时代、家庭、情感和大自然、村野的养育。他属于人类文化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传统,在这个传统中,所有以个人方式被其光荣地使用着的诗人,莫不是从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中得到启示,从最平凡人间的寻常快乐、苦难里洞悉生命之意义、宇宙之秘密。他们散落在世界各地,并出生在不同的朝代,却是来自同一个心灵基因清晰的家族,他们所有的理性都用来探索感受的秘密,并在这种感受中更新着人类的理性,推动人的心灵向善的艰难移动。
高银爱他的马,爱文义村和清水庄,爱雪后的大地。他的爱饱含着悲伤,因为时间在流逝,因为万物默默忍受着各自的命运。“死亡听着世间的人迹/远远走开又回头张望。/像今年夏天的芙蓉花/也像最谦卑的正义/一切都很低”。他如何理解“正义”这个词呢?正义在他的眼中是如此谦卑,是柔弱的,是在低处的。它不是革命者手中的斧子,也不是嗓门洪亮的吼叫,而是水声潺潺的流动,在夜里,在寂静的悲伤中。定义某事某物事关生死,尤其是“正义”、“自由”这样的词语,它影响着人们对于生活本质的态度和人之尊严确立的基础。诗人并非人间异类,他以表达可以共享的内心经验和内心感受成为最普通的人。他是一棵树,是一片出汗的稻田,是与死者同在的人,并且也是与死者一起活着的人。
他的诗中有神灵“我的哥哥死后涛声像哥哥
我丈夫死后涛声像丈夫
我的孩子死后涛声像孩子”
这是神灵在借诗人之口说话吗?还是神灵自己开口安慰失去亲人的人,它化为涛声,拍岸不息?可以确知的是,诗人是通灵者,是能跨越生死界限感知生命的人。死去的亲人只是变换了形体,化作涛声,化作尘土,化作风声——中国民歌《小白菜》中那个失去母亲的孩子知道,“我想亲娘在梦中,亲娘想我一阵风”;法国诗人雅各泰知道,“你曾透过地上厚厚的尘土/看着我”,而空气回答说:“他已变成了那令他最感到愉悦的形状。”生死轮回,无始无终,涛声风声,都是一曲悲伤的颂歌。
高银曾说:“中国古人相信土地不仅仅是泥土地,他们相信地有灵、有神的存在。树木生长出来,大象从其身上过去,刺猬到处去挖,土地之神都纵容它们。但是如果有人往大地上浇酒,大地就开始动起来了,开始舞蹈起来。用笔写诗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我在舞蹈。”高银诗中出现的乡野景物,在他的笔下被某种神秘力量唤醒,慢慢向人们呈现出世界的奇异本相——下雪了,在溪水里洗过的手脚,无家可归者在终点下车,一盏灯,东海几亿兆波浪苍茫,下雨时感到恐怖的初生工蚁……高银呈现的是努力与大自然对照的人间隐形结构,是充满象征意义的自然对人类社会的启示,是处于无限存在的宇宙万物的图景。在他那里,思想并非完全隶属于理性,人类对大千世界的感觉包含着思想,思想的激情是感觉烈焰的燃烧之物。充满童年的死亡的阴影,被放置在如此辽阔无垠的图景之中,获得的是悲伤的安慰——它依旧是安慰。甚至那覆盖一切、清洁一切的雪,也带给人悲伤的祈祷:“鹅毛大雪飘落/鹅毛大雪飘落,一切无罪”。
弘一法师诗云:“眼前大千皆泪海,为谁惆怅为谁颦。”高银写乡间的坟墓,写早夭的哥哥,患肺结核的姐姐,写每天走向死亡的人和牲口,写越战的伤残军人,写漂泊凄苦的妓女,这人间的苦难写得克制而充满温情,当一个人读到他“不要哭……我由无数个他者构成,不要哭”的时候,能不热泪盈眶吗?那融化心灵的感动,来自所有受苦人能感受到的诗人的陪伴,是“我是你,我是另一个人”的不再孤独。死亡,虚无,始终是高银思考的问题,在他的诗中,由于动人的深情,这一切都得到了一个温暖的安放之处。
他的心向着悲惨的人
在高银《很多人》这一辑中,他写到了许多命运悲惨的人:头顶大蒜赶往集市的贫穷女人,化作风筝的万洙的鬼魂,坐在轮椅中的瘫子女孩,被无耻的大人非礼的瞎子芬礼,那些畜牲们的爪子伸进了她的胸口……泪水和苦难,无言的顺从和无奈的反抗,那些哭声后长久的沉默,“这并非孤独而是信任/哪怕孤独也会长大的信任/独自玩耍/也与世界同在的信任”,高银不停地自言自语——如果不是这样,如果不是这样。这就是世界,这就是人间。
西蒙娜·薇依曾经说过:“痛苦造就了多少该下地狱的人。”仿佛是对这句话的回答,在高银的诗中,这些正经受着痛苦和羞辱的人,哀伤地守住了自己不滑向“复仇和杀戮”的道路。他们就像索德格朗说的那样,“仅仅像牲口一样忍受痛苦”。或许西蒙娜说的另一句话,正是来自宇宙最严正无情的规律——“无论发生了什么,至少这世界是圆满的。”对于曾是佛教徒的高银来说,因果之说能安慰这些受苦之人吗?抑或在人们对于苦难的忍受顺从中,也有着对不公平命运的另一种回答?那些“圆满的世界”里,一切苦厄都将以别的方式转换为未来的福报?而诗人的诗句就是易感的心灵为现世奉上的含泪抚慰——对于一个遭人鄙视的丑姑娘贵女,诗人这样写道:“我想做贵女家的人/我想在贵女家的厨房灶前/和她一起生火/我想去贵女大便过的茅房/也在那里大便。”这令人颤抖晕眩的诗句,怎不令人大放悲声!
他的人生与不公对抗
高银的诗尽管充满了禅思和深切的悲悯,但他并非像中国唐末那些因为愤世嫉俗而归隐的诗人。写隐逸诗在很多末世意味着抵抗、不合作,而像高银这样“勇猛”地对抗强权的诗人,人类历史上也不鲜见。上世纪五、六十年代韩国政坛震荡,每一次政权的更换都对异见者实施逮捕和枪毙。将人的命运视同自身命运的高银显然不会袖手旁观。尽管他自称“即兴”诗人,但这仅仅是创作的一个方法,并非他对个人、国家、民族的唯一感受尺度和区域。他曾写下过苏联时期诗人们面临的灾难,在《悲伤的第一人称》中,苏维埃诗人们将只能写“我们”而不能写“我”。高银敏感到:“启蒙很快变成了自相矛盾。”这位曾经的政治犯,投身于抵抗暴政的社会生活,用帕穆克评价加缪时说的话,对于这些诗人、思想者来说,“政治是我们被迫接受的不幸事故。”——“如果历史过于宏大/如果历史过于沉重 那就没有今天/……从观念的深渊中/从最崇高的错觉中/从夸张中/从虚伪中归来吧。”
历史终将被大自然回收。这是仁慈,也是人作为世界一部分的必需的视力。韩国批评家这样评说高银:他的诗歌凭借爱、愤懑、激情,在韩国诗歌史上开拓了“充斥于模糊感之中的直觉和灵感的领土,并扩张到日常生活的层面。”这就是诗人高银对人间不公的对抗,他哀怜的嗓音,来自一颗敏感多情、温柔的心。诗人的真实感受对任何权力来说都是一种威胁,因为感受所携带的复杂性在诗歌中还原着生活的真相,诗人的想象力抵达的任何事物,都在语言中不可避免地反射出他情感的深度和温度,它们是悲伤、是温暖,是大自然的安慰,是生离死别的哀歌,是这个冷漠和爱交织的世界的一份独特的见证——“唯有悲伤不撒谎”。蓝蓝(诗人)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看中华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看中华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