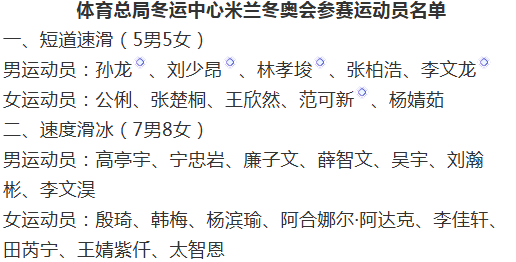改革开放四十年名家访谈系列 马大正:西域“行者”
看中华 最新资讯 2018-10-21 05:53:27改革开放四十年名家访谈系列 马大正:西域“行者”
谭洪安
1987年2月,马大正挥别工作了二十多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,正式加盟社科院创建不久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(以下简称“边疆中心”),担任中心副主任兼学术委员会委员。
那时候,他已近知天命之年,在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涯如此关键的节点上,决意调整自己的航向,不用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和决断的。
三十年后的今天,回首当初,现居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“高位”的他,看来并无悔意,笑言那是“我学术人生最有意义、最值得回忆的难忘岁月”。
那让我们看看,在相熟的朋友同行乃至后辈中人称“老马”的他,在事关重大而又相当敏感的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中,到底是如何识途的吧。
转向边疆
据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年简史:1977—2007》一书记载,1982年2月4日,时为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,曾就我国边疆沿革史研究等问题,致函李先念等高层领导人,“建议中央指定现有部门成立专门机构,进行长期研究,并下决心出一批书,这样才能培养新的专业人才,使我们遇到有关问题时便于应付”,避免“临时抱佛脚,事后就撒手,致资料无法积累,人才日见凋零”。
3月6日,李先念批示“同意胡乔木意见,应该重视关于中外关系史和中国边疆沿革史的研究工作”,“研究改进措施,加强这方面工作”。
大约一年后,即1983年3月19日,中国社科院边疆中心成立,由著名史学家、民族研究所顾问翁独健教授为首位主任。
翁先生早年毕业于燕京大学,后赴美留学,专攻蒙元史,193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,随即回国任教。共和国成立后,曾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市教育局局长,并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,1958年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成立,他出任副所长。“文革”中他受到不公待遇,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才复任副所长。而1964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民族所的马大正,就是他十多年的得力部下。由于有这一层关系,边疆中心成立之初,马大正作为“编外人员”时时参与中心的研究和资料整理工作。
据马大正回忆,1983至1987的四年间,边疆中心发展的步履异常艰难,究其原因有二:一是初创时期中心高度重视中国边界问题研究,但此类问题政治上较为敏感,资料搜集受到诸多限制,而且专门人才匮乏,研究成果也难以发表;二是边疆中心实际上是“多头管理”,繁复的商议与协调消耗了中心领导极大精力,却又收效甚微。
1986年5月28日,翁独健教授逝世,面临诸多困难的边疆中心处境更是雪上加霜。1987年2月14日,社科院决定将边疆中心改组为“院领导下的一个开放性研究中心,其行政工作划归近代史所管理,业务工作直接对院负责”,前期研究和组织工作表现甚佳的马大正,也因此由“编外”转正。
另据马大正的多年学界好友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学者李世愉忆述,1987年改组后的边疆中心,其实只有几个全职人员,租用的是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的民盟中央招待所,条件非常艰苦,除了几张办公桌、几把椅子、几个书柜外,几乎一无所有,真是白手起家。就在那种不利条件下,马大正与中心主任吕一燃扎扎实实共同努力,为中心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几年后,吕先生退休,马大正一人承担了中心的领导重担,可谓是呕心沥血。
马大正自己回顾在边疆中心工作的岁月时说,前期他既是一名研究人员,也是中心领导之一(1987~1993年),后期则担任主要领导(1993~2001年),其间大体上做了三件大事:一是为开展三大研究系列出谋划策;二是为当代中国边疆调查的展开身体力行;三是为中国边疆学的构筑尽心尽力。
十年苦修
马大正是地道的上海人,中小学教育均在上海完成,1956年7月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,那时候山大还在秀美的滨海港城青岛。大学生涯四年,经历颇不平静,1957年的“反右”,1958年的“大跃进”,1959年的“反右倾”运动,都在年轻的他心目中留下了不易磨灭的印记。
1960年7月本科毕业后,他获免试保送攻读山东大学(前两年山大已迁到省会济南)历史系研究生,师从近代史专家徐绪典教授。徐教授毕业于燕京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,曾供职北京故宫博物院,也担任过中国义和团运动研究会副理事长。得遇名师的马大正,研究生毕业论文题目就是《太平天国革命与英美传教士》。
1964年6月初,马大正结束了长达八年的学习生活,抱着立志争当“红秀才”的雄心,离开山大,赴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民族研究所(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前身)报到,步入当年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。但与大多数同龄的青年学人一样,在1964到1975的十年多时间里,身处研究机构、一心施展抱负的马大正,却长期与科研工作无缘,反而不由自主地翻滚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漩涡之中。他前后两次被安排到“四清”运动工作队,下乡参加劳动锻炼,第二次“四清”运动队集训刚结束,“文革”就开始了。那十年间,他时而是“革命动力”,时而又成了“革命对象”。
时过境迁,回首那段动荡的岁月,马大正颇感一言难尽。不过他说,那些年平心而论,确是经风雨、见世面、长知识,对社会真实观察和体会的加深,这也是大多数时间埋首书斋的社科工作者,特别是历史学者不可缺少的必修课。
1975年秋冬之际,转机不期而至,马大正得到了毕业以来第一个参与研究课题的机会——《准噶尔史略》一书的撰写,而这项研究的真正有序展开,已是“科学春天降临人间”的1978年了。
1982年,《准噶尔史略》完成后,他投入17至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政治史的研究,1984年,又参加了由翁独健教授主持的专著《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》的撰写,分工是隋唐民族史部分,并于1986年完成了书稿。通过上述两个研究课题,他对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富特色的王朝——唐王朝和清王朝的疆域与民族史事,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。
在此期间,他还担任《民族研究》的编辑,参加《中国历史大辞典》民族史卷的组织和撰写,与学界同仁广泛交往。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,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到1987年边疆中心实行重大改组,他走马上任,挑起构筑中国边疆学的重任,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行万里路
1982年,当《准噶尔史略》一书完成初稿后,马大正和研究同仁策划几年的“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计划”,在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(今历史研究所)和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支持下,得以付诸实施。
这是1949年以来首次官方组织的对新疆地区蒙古族的综合性考察,马大正的“天山问穹庐”之梦,由此开始了。
考察队于1982年6月15日在乌鲁木齐正式成立,当天即启程,至8月7日结束考察返回乌市,历时54天,途经15个市、县,18个区、公社和牧场,行程5523公里。
据马大正回忆,自1981年到2017年的36年间,他已61次到新疆,足迹东起哈密,北达阿勒泰、塔城,西抵塔什库尔干,南至喀什、和田、且末、若羌一线,还沿和田河自北向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,对天山南北风光有了实地感受。而1979年到2017年之间,他还共计赴云南34次。
“这实为人生的幸事!”他感叹说。
这61次奔赴新疆,多与他的新疆研究中如下五个重点有关:新疆卫拉特蒙古研究,瑞典探险家斯文·赫定新疆考察研究,芬兰探险家马达汉新疆考察研究,新疆社会稳定战略研究,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研究。
在1997年出版(后来数次再版)的记述1982年新疆考察之行的《天山问穹庐》一书开篇,马大正这样写道: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,中国治学的古训,我实践着。实地的访察,弥补了书本知识的局限,拓展了我的视野。”
这里且举他数访著名的霍尔果斯口岸为例。1982年7月第一次新疆考察到达伊犁时,因时间太紧,未能探访霍尔果斯,成了马大正一大遗憾。1986年8月借赴疆参加学术会议之机,才得以弥补。
霍尔果斯口岸,在清前期还是中国境内的驻防之地,同治年间(1862~1874年)中俄划界后,才成为边境哨卡。19世纪下半叶以来,这里一直是中俄(后为中苏)的传统口岸,20世纪50年代一度是中苏贸易的最大口岸。60年代中苏交恶后,霍尔果斯也成了“反苏前哨”,至1967年口岸基本呈关闭状态。
1983年,霍尔果斯又是首先开通的对苏贸易口岸。也许是开放未久,双方人员来往不频繁,1986年8月马大正看到的口岸现场仍显冷清。经当地边防驻军安排,他得以进入营房,登上高耸的瞭望塔,通过高倍望远镜观察苏方的边境农场。只见远处白色的木板平房整齐有序,鸡犬相间于道,一派平和景象,与以往几年他在数处中苏边境感受到的紧张气氛,已经截然不同。
四年之后,1990年9月,马大正再次走访霍尔果斯时,口岸的现代化建设初具规模了,国门两侧两国人员熙熙融融,生机勃勃。恰逢北京亚运会即将举行,国门中方一侧大标语牌上画着亚运会的吉祥物大熊猫。马大正见状不禁想:真是换了人间!
而近二十年后,今天的霍尔果斯口岸,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相邻,已成了东起连云港,西至荷兰鹿特丹的欧亚国际大通道的中转枢纽了。
“前线”“前沿”
过去三四十年,马大正投身中国边疆历史及边疆治理研究,他的最大心愿是,构筑一门新的学科:中国边疆学。
早在2011年7月,他接受美国《中国历史评论》(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创办的英文学术专刊)特约记者单富良采访时,就从当代中国边疆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视角,谈到了中国边疆的特色,认为大体可以从三个角度展开思考:
第一,中国边疆地区是我们国家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,漫长的历史留下了两大遗产,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,二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,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。当代中国的边疆和生活在边疆地区的各个民族,是这两大遗产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第二,中国的边疆地区是国防的前线和改革开放的前沿。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,中国的边疆就是国防的前线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边疆地区又成了对外展示中国进步的一个重要窗口。
第三,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,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。实践已经证明,改革开放以后,沿海地区飞速成长,中部地区也在不断崛起,如果西部地区跟不上,何谈中国改革开放的全局?
马大正解释说,中国边疆史研究的宏观历程,可以用十三个字来概括:千年积累,百年探索,四十年实践。
所谓“千年积累”,是指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,前辈学人留下了丰富的对边疆状况的记述和评议。所谓“百年探索”,涵盖了19世纪至20世纪200年的时段,中国历经巨变,改朝换代,民族危亡、民族振兴是这一历史时段的主旋律之一。期间的19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,外患挑衅日益严峻,西北边疆史地学兴起,此为中国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;20世纪二十到四十年代,中国面临敌寇步步进逼、亡国灭种的危机,“边政学”初露端倪,是中国边疆研究第二次高潮。
所谓“四十年实践”,指的就是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,中国边疆研究在新的国内国际形势下的大发展,可称中国边疆研究的第三次高潮,目前仍然方兴未艾。
马大正特别强调,对中国边疆研究学术成长史而言,1949年和1978年是两个关键的年份,因为这两个年份中国大地上政治的重大变动,中国边疆研究不可能不受影响。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,而就学术研究来说,1978年正是冲破极“左”干扰,让学术回归学术,“科学春天到来”的一年。
他认为,这一次研究高潮,一来突破了以往仅仅研究近代边界问题的狭窄范围,逐步形成了以中国古代疆域史、中国近代边界沿革史和中国边疆研究为三大重点(也就是前文提及的“三大研究系列”)的格局,二来突破了史地研究的专业范畴,将中国边疆历史和现状相结合,努力理顺研究与政策的关系。
壮心不已
2010年4月,时年七十二周岁的马大正退休了。但他个人感觉,退休对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没有太大影响,一切仍依常规在进行,因为“边疆研究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,只要身体条件允许,是不会中止的”。
早在2002年末,他受邀参加国家清史纂修工程,协助著名清史专家戴逸教授从事协调和组织工作,马大正说,他将此视之为一次难得的重新学习清史的机会。
在他看来,有清一代是中国疆域奠定和变迁的历史阶段,也是清政府边疆政策由成功走向失败的特定时期,一些当时困扰清政府的边疆、边界、民族等问题,到今天依然存在。从清代历史的总体性和以史为鉴的目的出发,有关清代边疆、民族方面的课题,理所当然要成为新编《清史》的重要内容,因此已专门设置《边政志》,以补民国初年编纂的《清史稿》的不足。
关于《边政志》,马大正想说的话不少:“历史上中国疆域范围及治理方式,是随着王朝国力的消长不断变化的。到18世纪中期《乾隆内府舆图》制定,中国历史疆域最终确立,当时陆地国土面积为1300万平方公里,其中边疆地区占到了一半以上。近代以来,中国边疆丧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,但今天中国的边疆省区仍占陆地国土面积的60%左右 ,可见边疆在历史上和今天中国的重要地位。”
“清代是中国历史疆域最终确立、集中国历代边疆历史发展之大成的时期,今天的边疆治理或边界争议中的问题,其源头大多可上溯至清代,”马大正说,“所以设专志记载清王朝在边疆地区治理和施政十分必要。”
今年9月,马大正年满八十周岁。每星期的工作日里,有好几天他仍然坚持穿过半个北京城,从东南三环的“自乐斋”家中,到西北海淀中关村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上班,而且不时长途飞行出差,继续“行走”全国各地,特别是辽阔边疆,精神矍铄,乐此不疲。
在今年3月编印的新著《学涯备忘》前言中,马大正写道:当然,研究工作优劣成败,应由社会评说,我只是做了自己乐意做的工作,在自己所在的岗位上尽了责、出了力,或者说没有虚度年华白了少年头空悲切!
而他萌生的最重分量的感言是:“我庆幸自己研究始步之时,即遇到了好时光。此言好时光,依我体会,第一是好时机——正逢科学春天的到来。”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看中华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看中华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